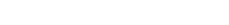正常与超常
——谈蔡志松的雕塑
彭锋
跟蔡志松结缘,是因为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那届双年展,我有幸担任中国馆的策展人。为了征服那个奇葩场馆(当时场馆里放满了油桶,根本没有展览空间。自第55届双年展起,油桶已被清走),同时为了与威尼斯的文化和环境发生关联(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东方带去的香料开启了欧洲的香水生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威尼斯仍然为水沟发出的臭气所困扰),我设计了主题为“弥漫”的展览,展出能够发出气味的作品。为了与中国思想文化相呼应,我决定展出五种气味,以便让人们回想起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五行、五味、五嗅等观念。我邀请蔡志松参加展览,本来是看中他做的玫瑰雕塑。我想在威尼斯展出具有东方韵味的花香。今天人们会普遍认为,象征爱情的玫瑰是西方的花卉,但是不要忘了玫瑰的原产地是中国。玫瑰花很好地体现了文化的迁移和交互影响,这正是我希望通过展览在威尼斯阐释的想法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方案的变化,最后蔡志松没有能够如愿展出他的玫瑰,而是临时创作了浮云雕塑,为那届中国馆增色不少。
在跟蔡志松讨论方案的时候,才知道他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早以“故国”系列闻名。蔡志松以风雅颂为主题的雕塑,将我们对远古时代的缥缈想象变成了结实的形象。就像荷马史诗塑造了西方文化一样,《诗经》塑造了中国文化。蔡志松的“故国”系列雕塑,开启了我们的文化追忆之旅,同时也唤起了我们对当代文化中的传统缺失的批判意识。蔡志松这个系列作品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优雅而忧伤,让人想起孔子对《关雎》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用玫瑰做雕塑题材,在当代艺术界中面临很大的风险。玫瑰花形状太美,它所象征的爱情又太俗套,这都是当代艺术避之唯恐不及的。蔡志松要将美而俗的玫瑰做成当代雕塑,就需要做出巧妙的转换。通过颜色、尺寸和材质的改变,蔡志松成功地做出了转换。铅板的灰黑、冰冷和有毒,与玫瑰的鲜红、热烈和友爱形成强烈反差。用铅板来雕塑玫瑰,既是对爱情的颂扬,也是对爱情的诅咒。正因为如此,蔡志松“玫瑰”系列雕塑的巨大语义张力就体现出来了。“玫瑰”系列雕塑,不是简单的再现玫瑰,呼唤爱情,同时还包含冷峻的思考、讽刺和批判。
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参展作品的基础上,蔡志松发展出了他的“浮云”系列雕塑。在雾霾笼罩的北京创作洁白的云朵,这既可以视为对现实的讽刺,也可以视为对理想的呼唤。蔡志松将作品命名为“浮云”,由此可见这个系列作品表达的,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失望。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征服自然,自然报以可怕的生态危机,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对于欲望膨胀、自然报应、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思考,成为蔡志松近来创作的主题。
为了准备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个展,蔡志松专门创作了“家园”系列。对于这个系列的作品,蔡志松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为了获得创作素材,蔡志松专门去扎龙自然保护区观察丹顶鹤,还从鹿场买来一对梅花鹿。蔡志松之所以选择鹤和鹿作为题材,是因为它们不仅是有灵性的动物,而是携带着吉祥的文化内涵。在传统绘画和雕塑中,鹤与鹿都是喜闻乐见的题材。不过,在推崇批判精神的当代艺术界,从正面来再现鹤与鹿的作品已经不太多见。不过,从反面来创作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据说即将在纽约古根海姆开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世界剧场: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就有三件作品因为涉嫌虐待动物而遭到抵制。正因为无论从正的方面还是从反的方面来创作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在时下的艺术界都有些费力不讨好,不少艺术家都回避动物题材的创作。但是,蔡志松是个例外。回顾“故国”、“玫瑰”、“浮云”三个系列的创作,我们发现蔡志松无不是从正面着手,将反思和批判意识融入其中。由此,蔡志松的作品与单纯的正面塑造和反面批判都拉开了距离。在“故国”系列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优雅与忧伤的并置;在“玫瑰”系列中,我们看到了爱情与死亡的并置;在“浮云”系列中,我们看到了希望与失望的并置。由于有了相反的语义的并置,蔡志松的作品显得含蓄而富有张力,而不是简单的表态或者站队。再加上蔡志松精湛的技巧,人们的注意力被作品牢牢吸引,而不再关注作品所传达的寓意。就像当年歌德与席勒的区别那样,歌德是从特殊到一般,席勒是从一般到特殊。蔡志松的雕塑与歌德类似。
在蔡志松新近创作的“家园”系列中,作品的语义张力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与“故国”、“玫瑰”、“浮云”系列相比,就制造语义张力来说,“家园”系列最为困难。尽管“故国”系列是以人物为题材,但他们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而是历史上的人物,表达的是我们通过人物对《诗经》的想象。因此,尽管蔡志松采用了写实的技术,但是由于其中渗透了历史的想象和虚构,作品与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同样,在“玫瑰”和“浮云”系列中,蔡志松也很容易制造张力。玫瑰和浮云本来就不适合作为雕塑题材,它们的脆弱和缥缈很难用雕塑语言来刻画。当蔡志松用特别写实的雕塑语言来刻画玫瑰和云朵的时候,本身就会给人以惊奇之感,而且在造型上也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但是,鹤与鹿不同。它们既是人们容易见到的真实动物,而且是历代雕塑家喜爱的题材,特别是被各种工艺美术程式化为十分僵化的形象。要在以鹤与鹿为题材的雕塑中制造语义张力,特别是如果采用的还是写实语言,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蔡志松迎难而上。他希望用宗教般的虔诚和精湛的技艺,将鹤与鹿的雕塑由散发匠气和俗气一般的工艺品变容为超凡脱俗的艺术品。蔡志松没有回避写实、工艺和美。他用比写实更写实、比工艺更工艺、比美更美的方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习以为常的鹤与鹿的雕塑转变成了不同寻常的艺术作品。被推向极致的精致和美,将鹤与鹿由动物升华为艺术,由一般的人造物升华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当作为雕塑的鹤与鹿的精神性与作为动物的鹤与鹿的通灵性结合起来的时候,蔡志松借助艺术和神灵来实现超越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作为动物的鹤与鹿的通灵性赋予了蔡志松的雕塑某种神秘性,蔡志松的雕塑又将鹤与鹿由动物提升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一种神圣的存在。蔡志松的“家园”系列雕塑的语义张力,不是来自正常与反常之间的冲突,而是来自正常与超常之间的不同。蔡志松作品的语义张力,在于他力图用正常的动物形象来表达超常的精神内涵,用可以塑造的形象来表达不可表达的内容。
2017年10月3日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